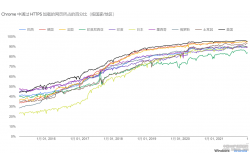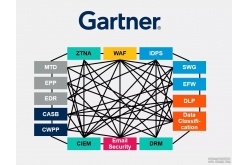发展大数据关键在于满足人的价值需求 行业资讯
早在1980年,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·托夫勒在《第三次浪潮》一书中,就将大数据誉为“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”。大数据为什么这么热?如何科学对待大数据?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。
人类第三次创世纪工程旨在建设一个新维度
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当前,“大数据”在业界和学界已成为“时尚”话题,人们认为“人类已进入大数据时代”,并赋予“大数据”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以“革命性意义”。在您看来什么是大数据?
姜奇平:我们不用工程师的语言,而从“人类”和“时代”这个角度,看看什么是大数据。我们今天所从事的大数据,只不过是人类第三次创世纪工程的一个片断。整个工程的“目的”,旨在建设一个新的维度,使“意义”投胎到世界的“数据体”上。为什么这么说?我们可以这样表达,人类曾投了三次胎。第一次投胎的胎体,我们称之为世界1。这是实体的世界,它以实体为中介存在。这个世界以功能和使用价值,承载人们生存的存在。第二次投胎的胎体,我们称之为世界2。这是价值的世界,它以货币为中介存在。这个世界将一切转化为等长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,即我们平常所说的价值。人们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,就是它“有没有价值”。这个世界以价值承载人们发展的存在。第三次投胎的胎体,我们称之为世界3。这是意义的世界,它以网络为中介存在。这个世界以意义承载人们自我实现的存在,要在以往的实用、价值的基础上,追求认同。
世界2是一个时空标准化的世界,它无法准确呈现意义的存在。今天,人们发明人际网络、物联网,都是在给意义一个适合的呈现空间,使事物隐含的快乐或痛苦的潜在含义,在我们创造的每一份价值和使用价值中鲜明呈现出来。大数据就是“意义发现”。通过意义的发现,指导价值的取舍,让有意义的价值实现,让没有意义的价值湮灭。
世界3的诞生,并不意味着世界2和世界1的消失。世界3只是相当于世界2和世界1的照明系统。传统经济相当于一个摸黑干活的系统,所谓“摸黑”就是指人们不知生产的东西哪些最终有需求,哪些没有,为此需付出巨大的交易费用,来实现供求平衡。“智慧化”相当于提供一个照明系统,让传统货币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再摸黑创造交换价值(世界2的价值)和使用价值(世界1的价值),通过大数据照亮意义,即洞察最终需求,只创造那些有意义的价值和使用价值。因此人们经常把智慧比喻成明灯。这是智慧化对于传统经济的意义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,大数据与传统经济并不是对立的关系,而是一个递进发展的关系。大数据的应用,本质上就是在世界2、世界1中寻找并呈现意义。
大数据旨在实现“意义”的专业化
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奥巴马政府将“大数据战略”上升为国家战略,甚至将大数据定义为“未来的新石油”。从当前及未来看,“大数据”究竟有什么用?
姜奇平:在这里就不介绍“大数据”细枝末节上的作用了,我仅谈谈大数据的根本作用,即实现“意义”的专业化。我先谈两个具体方面:
一是“意义赋值”系统的专业化。在大数据之前的世界,特别是工业世界,各种事务的功能系统、手段系统都是专业的,但一涉及意义,例如宗旨与目的,就变得十分业余。我们以智慧城市为例说明。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,智慧城市到底智慧不智慧,关键看它的“意义赋值”系统是否专业,有效还是无效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。就等于说,人民才是意义的赋值者。离开人民群众,就没有意义;数据离开了意义,就没有智慧;没有智慧,建设的所谓智慧城市就一定是愚蠢城市,与民生实际相疏离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大数据对智慧城市建设的顶层作用,应该是把群众路线专业化,让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、幸福不幸福这类意义信息及时被洞察、被满足,从而使人民群众得到更良好的体验。
二是企业决策系统的智慧化。大数据之前的企业决策,一线员工没有决策能力,这是意义系统不专业的重要表现。用户需求这种决定企业生死的意义信号,不能在此时此地的分散条件下得到当下响应。大数据让决策这种意义处理系统发生根本变化,从后台决策向前端决策转移,从集中决策向分散决策转移,从价值决策向意义决策转移。
举例来说,人们对大数据决策容易有一种误解,以为就是数据大集中的决策。这是传统集中控制思维方式运用到分布式计算条件下常有的惯性。
海尔的决策模式强调“群龙无首”。因为如果调动起每个自主经营体的主动性,使人人成为自己的CEO,这些一线员工就会进行分散CEO式的决策,没必要事无巨细非得通过“龙首”来决策。为此,海尔用战略损益表等制度,进行战略性的价值管理,使每个员工在决策时可以按企业的战略利益来权衡当前的形势,达到比集中式决策更优越的决策效果,其最高境界就是企业无为而治。
事实上,大数据决策应是集中决策与分散决策的结合。共性的问题适合集中决策,个性的问题适合分散决策。而且,二者不一定是对立的关系。例如,一线员工的分散决策,也需要并且可以调用数据中心的分析资源和计算能力;数据中心的决策,也需要与员工本地数据,甚至客户本地数据进行锚定和关联。按美国最新的情境定价理论,在一对一的营销中,产品和服务定价这种最关键的决策,可能要依靠用户本地数据,如手机中数据的参与,通过与数据中心数据的即时匹配来完成。用户数据参与决策将成为分散化决策的一个趋势。
不能离开人这一主体来谈大数据
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“大数据”作用的发挥,依赖于数据收集、数据提纯、数据判断等多重关键要素。但数据有时候也会骗人,有学者基于此提出,大数据“是一个过度包装的概念”,是个伪命题。对此您怎么看?
姜奇平:大数据当前确实存在包装过度的问题,主要表现在一些人把不是大数据的东西,都装到这个筐里,甚至夸大其作用,等等。但不能因此就把整个大数据说成是“伪命题”。
实质性的问题是,我们不能离开人这个主体来谈大数据。现在谈大数据,确实存在这样的倾向,而且这种倾向很普遍。例如,把“大数据”当作了“数据大”,这就确实接近“伪命题”了。因为离开了人这个参照系,很难判断数据是不是垃圾。
我认为,一些人看大数据的角度有问题。从数据这个角度解大数据,是客体的角度。仅从客体角度解大数据,缺点是难以聚焦,因为数据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,它们的存在是为了什么。所以,我建议人们换一个角度,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什么是大数据,也就是从大数据到底能解决人的什么问题这个角度,来看它是什么。这样看的结果,会发现大数据映射在主体上的是意义,是为了使人更好地获得智慧。对大数据来说,使人更能把握意义,就是智慧;干扰了人们把握意义,就是垃圾。
这个方向上的思考具有现实意义。许多专家都在提大数据的应用导向,就是在从客体供给导向,向主体需求导向转。不这样转,就成了为大数据而大数据,最后把要解决的问题丢了。这样的大数据,最后只会成为一地鸡毛、一堆碎片。更恶劣的是以搞大数据为名,其实是在为搞房地产、偷税漏税而服务,或者是套取、骗取国家有关资助,滥用纳税人的血汗钱。
我认为,“大数据”作用的发挥,不光有赖于数据收集、数据提纯、数据判断等多重技术要素,更关键的是应用,要同人联系起来,同解决人的问题联系起来。衡量大数据成效的标准,不应是TB这样的客体标准,不是创造了多少TB的数据,而应是利用这些数据,在满足人们需求方面创造了多少价值,有多大意义,这样的大数据才是“真命题”。
规避大数据过度发展的风险
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您认为“大数据”的负面作用有哪些?
姜奇平:“大数据”是中性的,谈一个中性东西的“负面”作用,需要补上这个问题省略的潜台词,才能让这个问题本身成立。
第一种可能,如果不能正确利用大数据,会产生什么负面作用?我认为,如果离开主体,离开人们的需求、应用搞大数据,会造出许多数据垃圾,不仅不会让人的脑子变得更清楚,反而会加大决策成本,让人们迷失在过多的数据中,找不到所要的答案。
为了规避为大数据而大数据的风险,第一要强调以人为本。搞大数据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提高人的洞察能力,使人变得更加智慧,至于发展技术、产业等次一级的目的,是由此派生的。第二要强调应用导向。对大数据,要抓应用促发展,以最终用户需求为导向,让大数据产生实效。要克服长官意志,让市场发挥配置大数据资源的基础作用。要避免只是从投入、供给角度片面发展大数据,最后弄出一些没有市场需要的政绩工程。
第二种可能,在大数据本身没问题的情况下,把大数据摆在不恰当的位置,或加以夸大,会产生什么负面作用?对此我认为,大数据在功能、价值和意义这一串价值链中,更多定位在意义上。意义要以功能和价值为基础,如果脱离了功能、价值而片面强调意义,负面作用是对整体产生虚化作用,也就是让事情不实在。
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:从中观上看,大数据产业的比重是不是越大越好?如何规避大数据发展不足或是过度发展的风险?
姜奇平:大数据产业比重不见得越大越好。它与产品制造业、服务业的比重应恰当。比重过高,就会出虚火。大数据作为产业,恐怕与经济的服务化程度有关,对农业、制造业、服务业等经济的服务化越发展,对差异化和质量提升的要求就会越高,对大数据的需求就会越高,大数据的产业链就会展开得越充分。而经济的服务化,也不应是人为决定的。一般在人均收入5000美元之后,出于对生活质量的追求,人们可能越来越多地把钱花在服务上。
为了规避大数据发展不足或过度发展的风险,需要的可能恰恰不是产业政策干预,而是要进一步发挥市场作用。美国《连线》杂志联合创始人凯文·凯利认为,未来人们会在个人信息保护与个性化服务需要之间达成均衡。对个性化的赋值越高,越倾向于开放个人数据,供服务者量身定制;相反,越不重视个性化(如只顾温饱),越倾向于保守个人数据,让服务者不了解自己。大数据的发达程度,显然与此机制有关。就中国现实情况来说,现在恐怕不是个性化供给能力过剩、服务水平过了,而是现有产业政策让同质化的中国制造产能过剩太突出了。因此,虽然从局部和短期看,一些地方发展大数据可能有点热,但整体上大数据发展还是不足的。